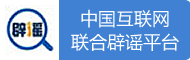夜宿化龙山
□ 任习波
人在化龙山,方能清晰感知到天光的起落。才看见西边山峰铺上一层暖金色,拐过一道山坳,那金光便倏然褪尽,只剩沉沉的天幕低低压着墨色渐深的树林。风也跟着变了性情,白天吹在颈间还只是微凉,这会儿却像带了刀刃,直往衣缝里钻。我们找了块背风的林间平地,地上是厚厚一层干枯的落叶,踩上去软软的。用树枝搭起简易帐篷时,林梢的枯枝在清冷的空气里相互碰撞,响声格外清晰。这小小的人造空间,在无边山野的暮色中立起来,像一颗偶然落下的果子,单薄,却让人心里踏实。
巡护时留下的痕迹,在渐暗的天色中慢慢模糊了。这里平时少有人来,只在小溪边看见几处零散的蹄印,大概是羚羊来喝过水。我把这些都记在巡护表上,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,成了这一天里最后一点规整的、属于“外面世界”的声响。收拾妥当,钻进帐篷,顺手用树枝半掩住入口,只留月光悄悄从枝丫缝隙间溜进来。
月光渗进来的速度是缓慢的。起先只是帐篷布上一小块灰白的斑,很快,那灰白便化开、变亮。我索性将遮拦的树枝拨开,一弯晓月已挂在冷杉树的枝头。不是满月,而是细细的,像一块被山泉洗得透明的冰,光也是清冷的、淡淡的。它不像太阳那样给万物染上颜色,倒像轻轻收走了山林的色彩,只留下黑与白的影,黑的是山脊与深谷,白的是曲折的岩石和远处峰顶的残雪;灰蒙蒙的,则是那片在夜风里微微起伏的树林。帐篷里暗着,我浸在这片清澈的月光里,自己也仿佛成了半明半暗的石头。
“夜色凉如水”的感觉,此刻真真切切贴在身上。白天行走带来的暖意早已散尽,凉气从地面一丝丝透上来,从四周无声地围拢。我裹紧睡袋,只露出脸。这凉是干净的、清冽的,带着松针和岩石的气味,吸进胸腔,像含着一块将化未化的薄荷冰。思绪被这凉意滤得格外清楚,白天那些纷乱的念头都沉下去,心里空荡荡的,只听得见自己平稳的心跳。
不知过了多久,一阵很轻、很慢的“沙……沙……”声,由远及近,像是什么动物踩着厚厚的落叶,走走停停。我心里倏然一紧,屏住呼吸听。那声音在离帐篷十来步远的地方停住了。透过帐篷的缝隙,借着月光,隐约看见一个比夜色更浓些的影子,不大,像是一只獐子或小鹿。它静静站着,头朝向这边,耳朵轻轻转动,像是在分辨陌生来客的气息。我们没有点灯,也没有生火,只有月光同样洒在彼此之间。它大概也在好奇:这一小团绿茸茸的,是新长出来的蘑菇吗?静静待了一会儿,那“沙沙”声又响起来,渐渐远去,融进了深沉的夜色里。我悄悄舒了口气,心里却浮起一丝微暖的安慰:在这深山中,我并未被当作闯入者,只是一个被悄悄打量过、又被默默接纳的过客。
后半夜起了风,不再是傍晚那种微风,而是贴着山梁滑下来的、带着寒意的风。它拂过林梢,掀起一阵低沉而又连绵的松涛,像远远的海潮声。风钻进帐篷边的空隙,发出“呜呜”的轻响,外头的枯叶被掀动,时不时传来“啪嗒”“啪嗒”的声响。气温似乎又低了些,寒意席卷全身。我把睡袋拉链一直拉到下巴,蜷起身子。帐篷里这方小小的空间,充盈着我和同伴的体温与呼吸,与外面那无边而清冷的世界,只隔着一层布。这脆弱的隔档,却让人感到一种格外的安心与温暖。在这与群山一同呼吸的寒夜里,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、温热的小茧。
迷迷糊糊中,一丝凉意落在脸颊上。睁开眼睛,帐篷里已是一片柔和的灰白。晓月不知何时淡得只剩一抹几乎看不见的影迹,东方的天边却透出一道极细极淡的鱼肚白,像青瓷边沿那一线似有若无的釉色,慢慢转成浅浅的金红。
鸟鸣先是一只,试探似的,从帐篷外的某根树枝上响起。接着,三五只跟着应和,嘀嘀啾啾,叽叽喳喳,越来越密,越来越响,最终汇成一首清澈欢腾的乐曲,彻底接替了昨夜幽深的虫鸣。天,真的亮了。
我从睡袋里钻出来,一股清冷又新鲜的空气迎面扑来,让人精神一振。走出帐篷,站直身子,深深吸了口气。草木和泥土经过一夜寒露的浸润,散发出一股沁人的、清冽的芬芳。化龙山正从靛青的底色中,一层层苏醒过来,显出朦胧而丰富的层次。那顶绿色的帐篷,静静立在那儿,像一个刚刚完成了任务、有些疲倦的伙伴。
我们卷起睡袋,收好行囊,昨夜那方寸之间的栖身之所便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只有我知道,群山也知道,那清冷的月光与寒冷的夜,曾怎样温柔地包裹过巡护的人,给我的心底留下宁静却温暖的慰藉。
一审:徐思敏
二审:田 丕
终审:张 俊










 陕公网安备 61090202000120号
陕公网安备 61090202000120号